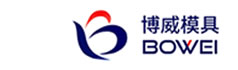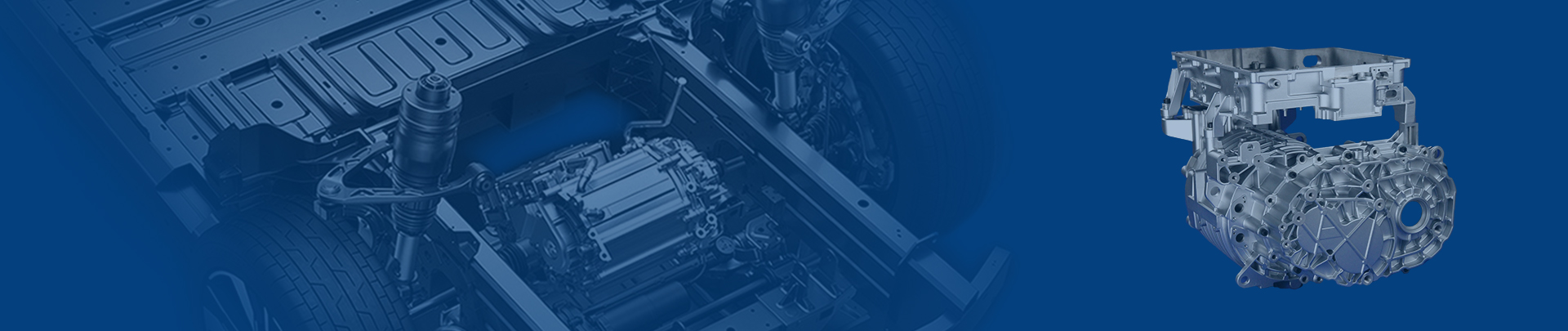《诗词中的战略思想》:探究诗词中的大境界和大战略
时间: 2024-01-24 10:41:10 | 作者: 医疗压铸模具
1945年,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应诗人徐迟之请,亲笔题词:“诗言志”。1958年3月,在成都主持召开中央会议期间,参观杜甫草堂,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我曾在杜甫草堂的简介中看到的这一评价,这对我理解诗词启发很大。说杜诗是政治诗时,难道自己的诗就不是政治诗吗?不从政治的角度看,我们肯定不能准确地把握诗词的精髓。
1973年7月17日,会见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说:“我读了主席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特别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我很想去看看。”说:“那是长征快完时写的。讲了一个片面,讲不困难的一面,……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如《诗经》,两千多年以前的诗,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我看,过百把年以后,对我们这些都不懂了。”显然对一些诗词专家对他写的《长征》一诗的解释不甚同意,就借《诗经》表达自己对“过百把年以后”人们对他诗词的解释也会遇到与《诗经》同样被误解的命运。纠正了人们对杜诗的附会和误读,我们后人也应当从政治的高度,不能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端正自己对诗词的误读。首先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的诗词文学性是服从政治性的。因此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诗词,可能最接近对自己诗词的理解;只有这样理解诗词,才可能在“百把年以后”防止后人“对我们这些都不懂了”的结果。
的诗词也可以有战略视角的解读,而不限于修辞、文学艺术角度的解读。阅读的诗词,我们会发现其中有许多是讲战略的。假如没有政治和战略高度,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诗词。
谈和他的诗词,我们就不能回避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认识全部作品最重要的切入点,的世界观与中国的成长是分不开的。我记得自己小时候的语文课本中有一段对话:在听到有西方人说是一个诗人时,我们的同志回答:不,他是一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这样的认识才是对的,不能把仅仅当作诗人,甚至仅当作一般的战略家,首先是带领中华民族实现解放的伟大领袖。
我们讲的战略思想,不能仅从所谓“谋略”层面讲,战术不能决定历史。战略首先是讲大势的学问,大方向错了,人的优点往往就成了缺点。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我们讲诗词,首先是讲政治,讲方向,讲战略。博弈中最终能赢得胜利的是事业的方正,而非一二奇招。奇招有效,但不可多用,初用可能盘活全局,然若无方正托底,复用多为死棋。1975年借用鲁迅的话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战略首先是审势的学问,既讲“形”更讲“势”。没有“势”,这个“形”就毫无意义。中国人常讲“势力”和“势利”,势有了,就什么都有。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他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今天也一样,只要路线正确,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可以有人,人们会因进步的事业凝聚到一起。正确的路线就是符合历史进步大势的路线。
学会把握和顺应历史前进的大势,这是我们学习诗词的重要视角。大势、方向决定一切。回想许多年前,中国有些“公知”对的事业总持所谓“批判”立场,但几十年过去了,结果如何?结果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树春”。社会主义中国不仅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而且在中国的领导下变得更加强大。
诗词文采斐然,自不用说,很多人都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诗词,似乎诗词“何等豪迈”“何等情怀”就够了。其实,只要是诗人,就都有情怀。可是跟其他诗人不一样,诗词讲的是政治。比如同是《卜算子·咏梅》,如果不从政治的视角,就读不出“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真意。
的真意是以他早年说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而陆游则以孤芳自赏为目的。两者意境,判若云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就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说的这句话是冲着黑格尔说的,黑格尔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提出:“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1975年7月15日,在听芦荻读诗时批评古代隐士:“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
杜甫和李白在唐诗中代表两种认识路线。李白的认识论的基础是佛学中的禅宗,禅宗是魏晋玄学与西传佛学结合的产物,禅宗本质是虚无的,禅宗的特点是只解释世界而不改变世界。
李白写诗就是写诗,没想改造世界,有很浓的禅意,李白的世界是虚无的。比如李白一方面赞扬秦始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另一方面又说“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而杜甫青年时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所以杜甫的诗中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比如《春夜喜雨》这首诗:
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春,这年杜甫已至天命之年。杜甫于先天元年(712年)出生于河南巩县,比王维、李白小11岁。他虽然被誉为天才少年,但是没有考上进士。杜甫年少时,曾游历吴、越、齐、赵等地。他虽然一路上作了很多诗赠予达官贵人,但始终未能出仕,杜甫因此生活困苦,只能将妻子儿女安顿在奉先县。最终他得到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一职,根据《唐书》百官志记载,这只是从八品下的小官。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被囚禁在长安长达9个月。至德二载(757年)四月,杜甫曾冒死逃出长安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并被肃宗授为左拾遗。但不久就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杜甫与房琯是布衣之交,因此被认为是房琯的同党。唐肃宗命令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一起审讯杜甫。幸亏有宰相张镐出面营救,还有御史大夫韦陟帮忙解释,杜甫才得以幸免于难。此后,杜甫被贬到华州(今渭南市华州区)。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夏,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广德二年(764年)春,严武再镇蜀,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给他做“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步入50岁后的杜甫基本放弃了从政的念头。
仕途多舛,知天命之年的杜甫对政治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如果从“政治诗”的角度阅读《春夜喜雨》这首诗,就会发现它是在总结杜甫自己的从政经验:第一二句说的是做事要恰到好处,如果不知时节,那就不是“好雨”而是“坏雨”——这两句包含了杜甫四年前因救房琯受到的与司马迁因救李陵所经历的同种遭遇;第三四句是说办事要知道借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善于等待上下共识的形成,有了共识,才可以“随风”成事。办完事后,不要出个人风头,更不要贪功——这时杜甫大概知道当年自己救房琯错在不会“随风”,即等待肃宗的共识。后四句是总结,说这样看似长夜漫漫,看不到明显成绩,但天明时就会发现“花重锦官城”,即收获满满。这是在讲从政之道。不求,上进;求之,不得。杜甫一生都以政治家为人生目标,想不到却事与愿违成了伟大的诗人。他的政治经验更多的是从官宦底层获得的。与近千年前的司马迁命运相似,杜甫在仕途路上颠沛流离,遭遇了太多的坎坷,官阶不高,但悟出了政治经验却鲜血淋漓并不自觉地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之中。看出了这一点。1958年3月7日,“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在杜诗版本展览室,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杜甫诗集说:‘是政治诗!’”
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那的诗就更是政治诗。读诗词不可能不与波澜壮阔的政治活动相联系,不从政治的角度而只从文学角度阅读诗词,那一定不得要领。
“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斗争胜利要靠我们自己的同志了解情况,和中国实际联系。中国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是在经历了重大牺牲后才获得的。一开始,很多人都是在上面漂着,结果让蒋介石拿机关枪逼着他们从天上钻到中国的土壤里,又从中国土壤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真理,这就是思想,从中国革命土壤中成长出的诗词才是诗词。
诗词是表达他所思所想的重要形式。诗词体现着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基于本人所具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越是困难的时候,诗词中越是充满着乐观情绪。
事情,事情,我们正是通过一件一件难事认识到并对产生深厚感情的;事理,事理,我们也是通过一件件历史难题认识所说的革命和建设的道理的。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和1935年,的情绪稍有低落。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重要的时期。1927年使中国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1935年与张国焘的争论及其后果使中国认识到中国地理政治学的重要性。认识地理政治学是认识中国实际的极重要的方面。很早就对学习中国地理政治学的重要性予以格外的重视。1915年他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方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以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1926年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他“讲述了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生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知道,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据《资治通鉴》,曹操取得汉中后,刘晔曾向曹操建议:“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在读到这一段时,在页旁批注:“不可信。”在读《魏书·刘表传》时批注:“做土皇帝,孟德不为。”且不说曹操的战略目标是逐鹿中原,也不说入川后因地形复杂将使清剿刘蜀政权的部队需要极大且因路途险远、运输而不能够确保的资源,我们只要看看13世纪中叶蒙古大军入川后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在今重庆)下以致终不能出川的窘境,再比较李自成出川和张献忠入川后的不同结局,就会知道,长征路上红军若进入四川也会陷入——用的话说——“瓮中捉鳖”的窘境。鉴于这些历史教训,在长征路上,才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张国焘西进四川的行动计划。不了解地理政治学的特点或没有地理政治学常识,我们就读不懂《七律·长征》中“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诗意。
再比如,读《念奴娇·北戴河》,就不能不了解中国东北及东北亚的地理政治学特点。“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此间,东北动则中原动,中原乱则中国乱。唐太宗、隋炀帝都注意到了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但都没解决东北亚问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在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没有把中国的安全利益锁定在山海关或中朝边境,而是将朝鲜人民的安全与中国人民的安全利益统筹起来考虑,也就是说保卫朝鲜的安全也就是保卫了中国的安全,对朝鲜安全的威胁也就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结果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压制在“三八线”以南——这确是“唐宗宋祖”乃至打败东北乌桓曹操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显然,如果不了解东北亚地理政治学之于中原政权安危的战略意义,我们就不可能读懂1954年夏填写的《浪淘沙·北戴河》。
唯物论和辩证法是一生始终坚守的认识方法,也是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根本原则。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战略是确定现实斗争方向的学问,而策略是寻找战略力量即国力运用边界(即极限和底线)的学问。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对立的方面规定的。过错,过了就错。过度运用战略力量是战略优势向劣势转化的开始。伟大的战略家就能正确把握自己力量边界的哲学家。只有寻找自我力量使用的合理边界,其战略才是有意义和可以有效实施的。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不仅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这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厚功底,更有成熟的政治素养——这需要高超地运用辩证法的能力。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1972年1月6日,同周恩来、在谈到正在草拟的《中美联合公报》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可以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通过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从政治战略上说,辩证法是矛盾转化的学说,任何强大的事物在辩证法面前都是要向自己的反面转化的。掌握辩证法的人就可以促成并加速矛盾的向有利于自己方向的转化。所以,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1958年12月1日,他告诉全党: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比如,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的所作所为,使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虑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根据革命斗争的经验,知道无经验的知识是书本知识构成中的边缘部分。好的教育是书本知识和经验的同时提升。现代应试教育的致命缺陷是人为地将受教育者从小与社会隔离并使之失去应对社会矛盾和斗争,特别是残酷斗争的经验。这样培养的人会像王明等一样,不懂国情,不懂人民,只知道一些书本上的教条,这样的人一旦上台,就会葬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鉴于此,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界“一从大地起风雷”,根据马克思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在学校教育中加大经验成分,以避免的恶果。如果不结合当时这些人才战略的思考,我们同样也读不懂1961年年底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其中“僧是愚氓犹可训”,指人是可以教育好的,但不能脱离实际,一脱离实际脑子就飘,一飘就必然会像赫鲁晓夫那样走唯心主义的道路。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召集康生、陈伯达等谈哲学问题,说:“哲学家要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想通过教育变革加强中国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并不是仅仅因为中国有儒学文化,而是因为有了和中国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如果仅仅停留在不加批判地接近儒家的所有思想观念,就可能陷入抽象人性论的窠臼。
赞赏的是“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即敢向“闻人”(今天叫大V)少正卯下刀子的孔子,反对的是由董仲舒抽去斗争性的孔子及其学说。即使如此,孔子的斗争性也不可能有阶级分析的高度,但如果将孔子的斗争性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那我们的认识论就会如虎添翼,形成较为强大的战斗力。认为,中国如果接受了那种没有阶级分析的“人”“人本”,乃至抽象“人民”的概念,就会模糊党的视野,找不准斗争的对象,其结果是越斗争,斗争的对象就越多,以致失败。
关注我们

官网公众号

官网公众号



 联络我们
联络我们